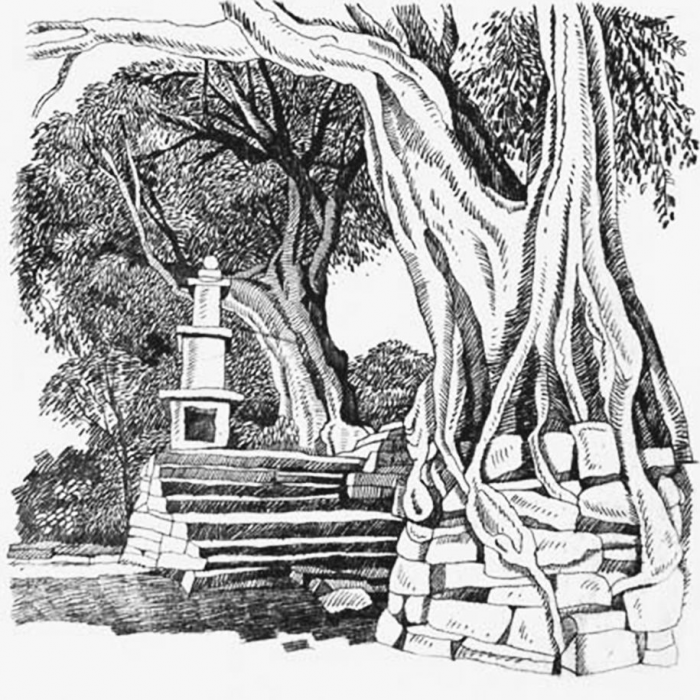
我是吃泉水长大的人。
那眼坐落在庄东头崖坡凹陷处的清泉,像山里的孩子一样没雅名,就叫无名泉吧!它被远近高低二三十户人家合围。一年四季,两三绺不急不缓的泉水扯落下来,汩汩涓涓,迸珠溅玉。泉水从岩壁一角的苍苔缝隙中倾泻下来,汇聚在下面石箍的方形大窠里。这口两三米见方的水泉不大不小,不深不浅,恰好可以高高地飘起三两只水桶,荡起圈圈涟漪。挑水时,成人曲腿蹲站泉边,用水担一头的链钩快拉桶绊,桶斜水满。吊起桶身,拉上泉边,回望泉水,光影斑斑驳驳、荡荡漾漾,沉渣一点不起。
无名泉正上方的坡台上,住着一户散落在树林里的人家,靠近水泉,却远离人群聚居地。
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小学教师,他的媳妇莹莹姐心灵手巧,热心肠,是大家喜欢的人。
莹莹姐能用任何纸片迅速剪出你要的图像,能在锦缎布脚面料上一笔画出刺绣图样。她经常帮人扎绣缝制姑娘嫁妆:绣花枕头,门帘襊檐。她还会给满月的小孩扎缝老虎枕头、老虎暖帽、莲花帽圈。我最乐意跟在母亲身后去莹莹姐家,不是为看莹莹姐给大人们画纤纤巧巧、藤藤蔓蔓的花草,或指点针脚,而是要她用彩纸一气给我剪松鼠吃葡萄、猴子吃烟、喜鹊闹梅。母亲、姐姐也能剪,但莹莹姐剪的手法更好看。
在大人忙针线的时候,我喜欢拨弄莹莹姐缝制的老虎枕头上的圆眼睛。这一双溜圆的大眼睛,用五色彩线打结成毛茸茸的眉毛和精致纹理的眼圈,里面眼珠镶嵌的是指肚大小的镜片,上下左右晃动,闪亮照人,灵动可爱至极。
最早遇见住在水泉下村子里的柳海英,是和外祖母抬水途中的歇息时。
抬水路绕行在高高的崖坡上,极目下望,一马平川的田畴尽收眼底。在坡根墨绿色的麦苗地里,一位正当壮年的妈妈领着一大一小俩小子在锄地。大男孩高高瘦瘦的,干活沉静持重,像一个小大人。小男孩虎头虎脑,提个篮子满地跑,时不时在地里翻筋斗。外祖母远远地和他们打过招呼,就絮絮叨叨攀谈了起来。
大人们时刻不忘记的热心事是给身边的孩子攀亲家。我和柳海英很快被外祖母和他妈妈隔空喊话,编排成了一对。柳海英当时懵懂至极,被说成和我一对,丝毫未开化,继续在麦苗地里疯玩。我也忙着捻花玩草,连他的眉眼都没心思细看。因此,对柳海英我没有特别印象,但记住了他的名字。
吃着泉水的孩子容易长大,我很快上了初中。有一天,从小学一直交好的同学桂莲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借到了一本很好看的书《法国爱情短篇小说选》。我问从哪里借的,她说柳海英家,他们两家是邻居。
我心中一怔。
柳海英的哥哥是川道里出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这我知道,他们兄弟竟然是桂莲的邻居!
我觉得《西游记》《水浒》《青春之歌》是最好看的书了,没想到桂莲从柳海英那里借来的书,更精彩无比。《法尼娜·法尼尼》让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美丽和英俊叫金发碧眼,意大利的烧炭党人也和林红、卢嘉川一样机智勇敢,视死如归。最让我无法言说的是《嘉尔曼》的悲剧带来的震撼(许多年后才知道这篇小说就是著名的音乐剧《卡门》的蓝本)。从此《猎人日记》《复活》《大卫·科波菲尔》也走进了我的视野。
柳海英上初三,我上初一。那时的柳海英帅气阳光,是学校篮球队的男篮队长,周围应该有迷妹,他没工夫回望身后的小学妹。但我却通过桂莲蹭读了他家许多书,上完学我们慢慢走散了。即使外祖母和他妈妈铺垫的故事未演绎圆满,我依然感激与柳海英相识相遇。
离开家乡我很久没有故地重游了。听桂莲生活在老家的父母说,无名泉已经不出饮水好几年了,去年竟然断流了。泉上的莹莹姐家也搬到平地大路边去了。莹莹姐也该老去了吧?泉下的柳海英兄弟,哥哥海志大学毕业娶了她们家东边同队的姑娘金枝,去了克拉玛依。海英在西安。金枝姑娘是上下川道里,水一样美丽的女子。
泉水叮咚在耳边,脚步散落在寂寞的长路上。也许我们最初出发离开,最大的意义不是能有最好的遇见,而是回观来路时,发现最好的遇见,可能一直在眼前,甚至在身后。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