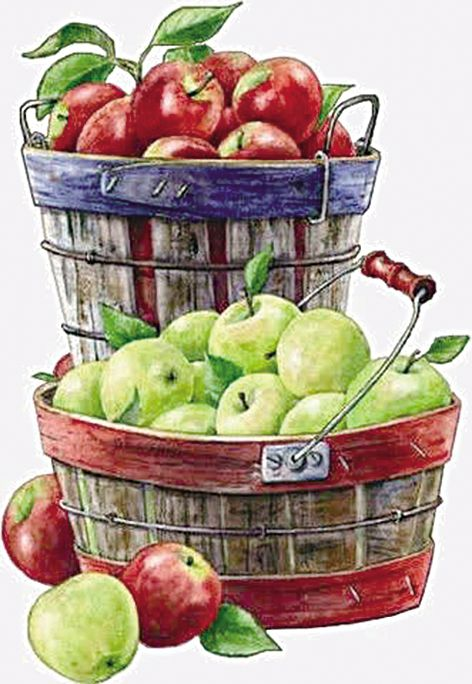
八五年隆冬的一个午后,北风呼啸着卷起巷道里的烂树叶和塑料纸,阳光惨淡无力地照着一堆堆干牛粪。
我们村大队部社员会刚刚结束。
父亲说:“上塬的60亩地给社员承包了,让栽苹果树,我包了5亩。”
“栽苹果?行不行?赔了咋办?不要弄几年把苦下到榆树底下不说,村里人还笑话。”母亲带着疑虑。
“我看行,书记、村长、会计都承包了,村干部都觉得行的事儿,没问题,等果树挂果了,娃也大了,念书得花大钱。”
次年阳春,父亲和叔叔们拉回了苹果苗木,仔细平整好土地,把长长的绳子拉直,端着白灰撒线确定行和列。不几日,满地都是方方1米的大坑,60多亩地的摊场,很是壮观。
四季交替,定杆、拉枝、除草、涂白、修剪、施肥,父亲在果园里没黑没明地干活,我知道,他是高兴的。他熟悉果园的角角落落和每一棵树。
采摘季节,大人和孩子推着车车,挑着筐子,倾巢出动,几十口子人拥进同一块果园里,呼喊声、笑骂声此起彼伏。女人们胸前挎个布袋子,小心翼翼地摘苹果,壮年男人用扁担把一筐筐苹果担到集装点儿,老人们在小山似的苹果堆旁边捡拾不合格的次果,孩子们“挑肥拣瘦”边吃边玩。大家伙是同村乡邻,彼此熟悉脾气,不怀好意的大兄弟开着小嫂子的玩笑,每每这时候,长兄们会装得死气不出,越是这样,越逗得大伙嘻嘻哈哈,我们总是装着听不懂。
那时候父亲年富力强,无论装谁家的苹果,总是拣重活干,担苹果、上树摘、过大秤、装上车,没黑没明地忙碌。
专家说农家肥是苹果生长最好的肥料,秋冬季,父亲会雇一辆四轮拖拉机,连续数日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拉茅粪回来灌苹果树,每日拉四五趟,早早出门,中午凑活吃一点,黑隆隆的晚上才回到家,浑身散发着难闻的味道;专家说树下铺麦秸,父亲就给地里铺满麦秸;专家说种三叶草保墒,绿油油的三叶草沾着露水总是打湿父亲的布鞋,真是能成的精都成遍了。
有一年,苹果赊销给店头街一位王姓果商,直到腊月,大家跑了五六趟,一分钱都要不回来,眼看过年了,钱没有,年难过,果商媳妇嘴里还胡说。大家吵吵着要起诉果商,6个人分成两派,争执不下。父亲和另一个叔叔没有去打官司要钱。其余4家的钱不久就通过法院调解要回来了,我们就怨父亲。父亲说:“行情不好,老王也赔了,咱不能把人往死里逼,他说开春起来会给的,打交道这么多年了,都是本地人,不会不给的。”果然,来年四五月份,果商带着媳妇,提着烟酒,把钱如数奉还。
大约2000年,父亲又栽了6亩果树,挖通壕、铺地膜、集雨窖灌,果园就像他的小儿子一样成了宝贝蛋蛋。
暑假,政府倡导果园里挖水窖,把公路边的雨水引流到水窖里,便于旱季浇灌和取水喷洒农药。酷暑,地上炎热,窖里湿热,我和父亲常常光着膀子,一个人挖土,一个用绳子吊上来倒掉,再挖,再吊,二十多天,我们用一把小 头,给两块果园挖了两个8米深的水窖,单个存水量30立方米左右。
父亲爱果园,更心疼我单薄的身体,干累了,就让我歇着,他又把挖上来的土运走。那个假期,我学会了喝茶,和他一样泡一杯浓浓的茉莉花茶。
第二块果园的苗木是我一位朋友送的,丰收了,父亲满满装了两大箱苹果,饱满到胶带封不住箱子口,让我谢谢朋友。
我说:“人家在果业部门,不稀罕。”
他说:“这是咱的心意,不一样!”
这块果园,撑起了弟弟妹妹读书的梦想和全家人的吃喝用度。
有一年,苹果不好卖,果商精挑细捡,半早上,装进箱子三分之一,其余都剩下打入次果。父亲终于发了一回火,骂经纪人把良心死了,骂挑苹果的人眼窝瞎了、饭都让一个个白吃了,停了!就是烂了臭了都不卖了!
装起的80多箱在窑里堆放了二十多天。
一日,父亲打电话很急切:“你在哪儿?往回走!狗日的果商来装车,说我把箱子里的好苹果倒换成烂苹果了,还报警了。”我知道父亲的为人,但又怕他吃亏,就急急回村。
我的父母、警察、村干部、果商、代办和一些看热闹的乡亲聚集在村支书家。果商说:“苹果不对!”父亲说:“狗一个一个口说人哩,谁把苹果倒换了,把谁死了!”
看得出,父亲是受了莫大侮辱后,有一肚子气。
我说:“不要急,让公安查,要是查出来苹果被倒换了,我们十倍赔偿;要是造谣污蔑,我父母有啥闪失,对不起,你们得承担一切后果。”
警察现场也品出了一些渠渠道道,说了几句硬扎话:“一旦立案,就得抓人!”
经纪人一看阵势不对,便说了些软话,果商给父亲赔了不是,便督促装车、付钱、夹着尾巴逃跑了。
经年累月的劳作,父亲60岁后,腰就疼得厉害,抱苹果箱子和上梯子套袋等活儿便做不来了。
一天,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又折腾着给沟畔一亩多地里栽苹果树,让我管管。我笑着说:“他爱栽就栽吧,你管了他一辈子了,你都管不住了,我也管不住。”
原来,子女们一再嚷嚷着不让经管果园了,父亲闲不住,就栽一块小面积的,自己找个事,产的苹果儿女和亲戚们够吃,剩多少卖多少,多少添拨一点零花钱就行。
如今,70岁的父亲,第一块果园挖了,第二块果园承包给堂叔了,自己经管着小果园四五十棵树,就像陪着一大群孙子优哉游哉地走过日出日落。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