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专业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三、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首届朱自清文学奖,首届鲁艺文学奖,首届“漓江年选”文学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敦煌文艺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2012年《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第三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2015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以及《青年文学》《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榜等重要榜单,入选“新世纪20年青年作家20家”。

文化艺术报:在众多年度排行榜中,《收获》排行榜有着很高的公信力,这和《收获》杂志的文学品质有关。这是您第四次登上《收获》文学排行榜了吧,您是如何看年度排行榜的,和上榜其他排行榜的作品相比,您更看重哪一个?
弋舟:《收获》无疑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是自巴金先生始,几代“收获人”耕耘的结果,在文学界内部,甚至有“没在《收获》发表过三篇以上的小说,就不能称之为小说家”之说。《收获》文学排行榜的榜单,在相当意义上集合了每一年度文学现场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成绩,四次入榜,两次登上短篇小说的榜首,能够跻身这样的序列,对我而言,当然是与有荣焉,甚至,这样的表彰,就是给予我的最好的文学温暖。如今各种文学榜单层出不穷,我个人觉得未尝不是好事,至少有益于引发社会对于文学的关注,当然,无论怎样,评出的作品要有公信力,要经得起检验。除了《收获》文学榜,这些年我也有幸多次入榜其他的榜单,我难以说出自己更看重哪一个。一个排行榜的分量,更多地,应该是交由公众来衡量的吧。

弋舟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您是各种文学榜单的常客,今年上榜《收获》排行榜的短篇小说《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是您今年重要的作品。您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个短篇的写作契机是您从飞机上看到一个新闻,先有了小说的篇名,然后“生活中所有的瞬间”都成为了事件,成为了文学,类似的篇名先行,好像在您不是第一次,这会不会在写作中造成主题先行的困惑?
弋舟:这个短篇的写作契机的确是由此而来。所谓“篇名先行”“主题先行”,听起来似乎有些“不正确”——因为你对我有着“困惑”的担忧。这样的问题,在具体的写作时刻应该是不存在的,否则我也不会一边“困惑”,一边倔强地劳作。文学是如此难以谈论,如果你会因之“困惑”,那你就去写“不主题先行”的作品。我们无需对一些概念纠缠不休,写,并且写好,是第一位的,即便我们很好地解决了“什么先行”的问题,写出的东西令人不忍卒读,那又怎样呢?写作的唯一“正确”,大约就是“写好”。

文化艺术报:您的作品,很多都要写一句献词,《刘晓东》献给母亲,《平行》献给父亲,《雪人为什么融化》献给姐姐……在《丙申故事集》中,您甚至“再一次永远地献给妈妈”。这些虚构的故事,和血脉相连的亲情之间,有何关联?
弋舟:这的确是一个小说家的“私情”。但我想理解起来也不会特别的困难。毕竟,我们还是赋予了写作之事某种崇高感的,将崇高的事物奉献给亲人,既表达了我自己对亲人的爱,同时也敦促着我在写作的时候“自我确认崇高”。我觉得可能后者更重要一些,一旦想象我的写作要交由亲人来检验,我的笔至少就不会过于散漫和懈怠吧。我所说的“交由”,并不是说一定会让他们读,更多的意思是那种精神的交托。写《丙申故事集》的时候,我妈妈已经离世,事实上,她也无法读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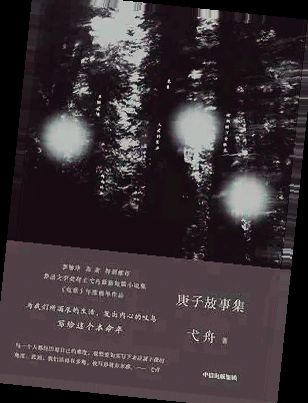
文化艺术报:您的人间纪年系列,坚持了多年,到今年的《辛丑故事集》,已经是第四本了,为什么会坚持写“人间纪年”系列?这种写作方式会不会打乱您的创作思维,为了完成而舍弃您最想写的作品?
弋舟:说起坚持的动力,可能也并不复杂——我是个作家,我就得写作。不惮庸俗,我还可以如实相告:我需要以此养家糊口,以此得到朋友的喜爱等等。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写作”,于是也不存在“写作打乱写作”。我们往往不免赋予自己尚未开始的行动以更高的价值与意义,好像有一个更为重大的目标有待我们去实现,藉此来贬低我们此时此刻的劳作,或者粉饰我们此时此刻的无能。这样想,不能说完全有害,至少也是无益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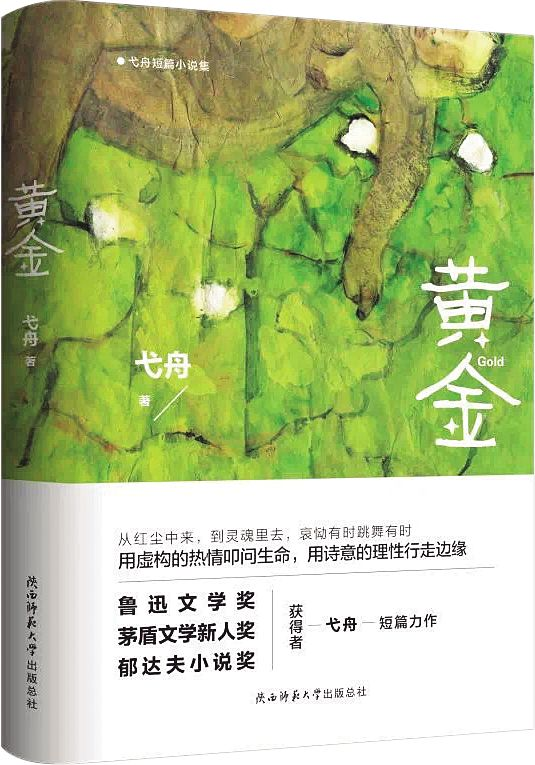
文化艺术报:您的文学语言和讲故事的方式,都有很强的辨识度,甚至有人说“弋舟是心理现实主义作家”。您是如何在心理和现实之间通过小说构建您自己的心灵世界的?
弋舟:现实永远是我们虚构的起点,但这个起点需要经由我们的心理来感知与辨识,两者从来就不会是截然对立的,毋宁说,它们本来就是一体。在很多时候,现实是公共的,它就摆在那里,但经由每一个人不同的感知之后,现实其“意义”,才有了不同的面向。就我而言,不过是忠实地以己之心去呈现了我所认知到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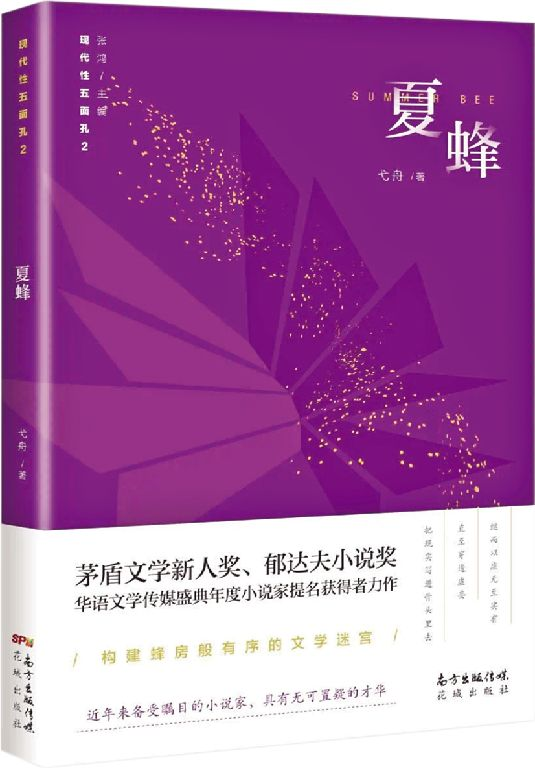
文化艺术报:在您的写作中,艺术至上一直是您的标杆吗?
弋舟:“艺术至上”“标杆”,这样的描述,如今是我不太愿意接受的,年过半百,我大约也知道了,相较于写作,生命还有太多的重要向度。
在延续自己的写作理念和立场这一点上会遭遇很多难题。前阵子和朋友聊天,还聊起《耶路撒冷三千年》,我说中国作家今天已经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才华,而是没有这样的耐心、从业精神和基本伦理,这种真正甘于把生命、把精力全部押在作品上面的能力很弱。到一定阶段,会突然觉得有些凌空蹈虚的东西,会想去切身验证。卡尔维诺有一个故事《树上的男爵》,住在树上当然很高级,但从树上下来、在大地上奔忙也是人的标配状态。我们很难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格缺陷,但同样我们需要思考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愿望和捆绑你的东西时常会打架,这种摆荡渐渐地在我心里越来越多,可能以后小说的面貌还会发生改变。

文化艺术报:您曾经说过,您这一代作家,一直在抵抗仅仅运行于故事层面的小说。这种抗争有没有意义?早年的先锋作家也抗争过,但最后要么不写了要么妥协回到讲故事的路子上来了。您抗争的是故事还是仅仅运行在故事层面的小说,这种小说在今天依然活跃在各种主流期刊上。
弋舟:这样的话,似乎是放肆地说过。反抗故事,或者过度地反抗故事,由此带来的问题,如今已不言而喻。彼时如此,一定是隐含着高下的判断,但是今天,这种判断重新摆荡到了对于故事的尊重。但彼时的反对并不意味着全无道理,仅仅于故事层面运行的小说,如今显然仍在甚嚣尘上。但“没有意义”显然是不对的,不知道是否真的原话如此。现在,我既不抗争“仅仅运行在故事层面的小说”,更不抗争故事。而且,我也怀疑自己是否使用过“抗争”这样的词——它不太像我的语言习惯。至于“活跃”和“主流期刊”,如果的确是个事实,那又怎样呢?还是那个观点吧:故事与否不重要,写好才重要。

文化艺术报:评论界一直把您的创作归于城市文学。到底什么是城市文学,恐怕评论界自己也难于说清楚,您是如何理解城市文学的?
弋舟:被“归于”,想一想一定也是有道理的。我的确没有乡土经验,所写的,也多是城市生活,至于“什么是城市文学”,既然连评论家都难以说清,我们就不费力去琢磨了。我所理解的城市文学,也无外乎:写城市,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现在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一天农村生活的经历,让我写乡土文学是不现实的,但我写的真的是城市吗?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写的依然是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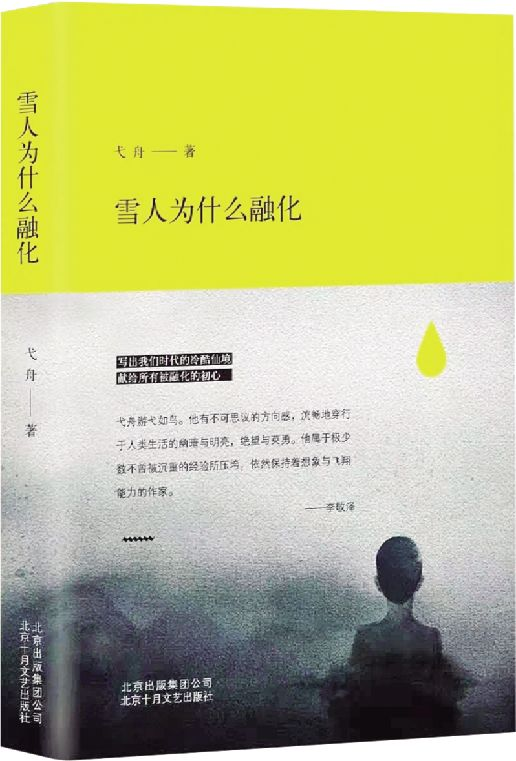
文化艺术报:您说“一个好的作家,理应具有追求经典并成为经典的抱负,同时,也理应培植自己发现和指认当代经典的愿望”。在您看来,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有哪些能称为经典?
弋舟:已经不少了,我们也无需妄自菲薄,《白鹿原》不是吗?《秦腔》不是吗?那一代先锋文学的前辈们写下的杰出篇章,不是吗?

文化艺术报:您从兰州回到陕西,一直坚持自己的文学风格。在陕西这块现实主义文学的阵地,所谓的宏大叙事、大气象、人生问题、终极关怀,这些需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写来实现的现实主义,和您的文学理念会不会发生严重冲突?
弋舟:当初回来的时候,我将回到西安认定为归队与还乡,由此我的写作必将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那个曾经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漂泊个体的写作者,从此将要扎根,让自己与浩大的生活发生更为自觉的联系,让生活本身成为自己文学生命最为可靠的源泉,这也是我重回陕西的重要文学动机。没有冲突。我常说,“人应当缺什么补什么,而不该有什么放大什么”。如果你认为我的风格叙事不宏大,气象小,不涉及人生问题,缺乏终极关怀,那么好了,我好好学习补充就对了。
我在兰州生活了20年左右,而且这20年对于我这个具体的个体生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20年。从年龄状态上说也是最好的20年,而且和我个人的写作时间合起来,也就是从兰州这个地方我开始写作,渐渐走向成熟。回到西安之后反观这两个城市,我们经常会发现,当你在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对它充满了偏见,所以人人都有想要逃离的心情,但是你一旦离开,你重新再去回望和眺望它的时候,甚至又会涌起某种眷恋。
至少目前我这个生命个体是主要和这两个城市发生关系,可能也就是这种恰恰有比较鲜明的不同,构成了我写作的某种特征:不太完全像一个中原地区的作家,也不太完全像一个边疆地区的作家。

文化艺术报:您专业学的是美术,最初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从绘画转向写作?
弋舟:如今我越来越难以十拿九稳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我的经验,个人生命的轨迹,实在是难以给出某种“自我决断”的路线图,就是说,那不是“选”出来的,更像是“被选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成了今天的我们呢?好吧,这是命运的选择。
如果将写作这件事以“个人书写史”的自大追根究底,那几乎可以追溯到童年了。我在小学获得过市里作文比赛的奖项,这可能给了我某种能力的暗示;大约在十三岁的时候,向《收获》投过稿,这个经历在《收获》六十年的庆典上我还坦白过,坦白之时,竟也略感唏嘘。若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计,这些都是不能作数的。
在将近而立之年时我才投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是时间,是天性里对于时间的敏感,敦促我写起了小说。而将一件事情的缘起交由时间之因,这本身就像是在诉说命运吧。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孟繁华经常在您的作品中读出“一个游子,常年在他乡的孤独感和无根感”。他以小说《随园》为例,“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对人生的设计都有一个线路图,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没有走在这个线路图上,所有人仿佛都‘一脚踏空’,最终直指对人性困境、道德困境、人生终极问题的关怀和追问。”您是如何看待您作品中大水一般弥漫着的孤独?
弋舟:没有任何个体的悲欢可以逃脱时代给出的基本限定,“普世的况味”是文学作品产生共鸣的条件,也是衡量文学作品品格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常识,我们竟常常罔顾。写作者的确存在这样的风险,过度沉浸在某种不能被人理解的自我之中,拧巴,封闭,沾沾自喜或者自怨自艾,在自说自话中完成自我的神化。但我们又不能以此忽略时代之下个体的精神吁求,所谓见微知著,正是文学的要求。
如何将个体与时代形成映照,这挺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我有一部分作品,在命名上就做着努力,譬如《我们的底牌》《我们的踟蹰》《所有路的尽头》,这些篇名以“我们”和“所有”的名义书写一个个具体的人,至少是在给自己一个暗示:你写下的张三和李四就身在你所在的这个时代里,他们是与你休戚与共的,是与你共同构成那个“我们”中的一个。
我觉得尤其是男女的情感方式,是能够折射出每个时代的不同气质的。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像汉朝人一样谈恋爱了,与革命时期的爱情肯定也不相同,那种对于爱情的基本相信与持守,可能也在动摇,但人类对于爱情的盼望、对于那种爱情理想本身的向往仍未消减,于是在恒久的盼望与追求理想的落差与张力之间,涌出了苦恼的源泉。这种创痛性感受,基于人性,又与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没有更大的感知力,可能终究都不会弄明白自己的那点儿难过和伤心是因何而来,你爱着的人为什么不爱你了,你不爱的人为什么还是要在一起,这里面有家长里短、油盐酱醋,其实也有时代的内在律动。
这种笔下人物的痛苦,看起来往往是无端的,没有所谓现实逻辑的必然——他们丰衣足食,苦什么呢?是什么戕害了他们?也许我们太迷信那种其来有自的事物了,但这世上就是有人在无端端地哭。我们没法再像前辈们那样去书写苦难了,饥饿,战乱,甚至失业和失恋,给那些苦难轻易地赋予正当性,但这些“正当性”,就能反证大观园里那群男女之苦的不正当吗?这种“精神上的苦难”,搞不好,会显得无病呻吟。如果出现了这种效果,要么是作家没写好,要么是阅读者不被一根现实之针扎在指尖里,就无从想象那永恒的疼痛。

文化艺术报:您的短篇小说《出警》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这样的大奖给您带来了什么?
弋舟:获奖消息传来的当天,我正在给母亲扫墓,这无论如何对我个人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我的母亲一生怀有写作的梦想,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出要将我培养成一个作家,但自己的儿子写出了被人认可的文学作品,一定符合她的美好憧憬。获奖在这个意义上就几近“私事”了,算是我对于母亲养育的一个报偿,更多地,我也愿意在这个意义上鼓励自己,写作的路那么长,怀有一些切己的“私意”,自己可能就会更有韧性一些吧。
文化艺术报:著名评论家白烨说“陕西太缺弋舟这样的作家了”,与陕西本土的作家比起来,您“洋气”,作品直指人心,直指人的感情深处。他们同时也希望您能够靠近,继承陕西文学的传统,您会接受这种观点吗?
弋舟:白烨老师太爱陕西文学,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他这番话的意思,可能也是在强调“人应当缺什么补什么,而不该有什么放大什么”,所谓“取长补短”,所谓“吐故纳新”,都是生命本身的常识。如果当真如此,只能归结于血脉深处那些玄奥的基因了。
文化艺术报:您在一篇文章中强调“希望自己的小说是体面的”,这个“体面”有没有特别的指向?
弋舟:对此我有过解释,那大约是:这个“体面”,一定不仅仅指向某种娇柔的风雅,更多的,是对艺术本身的敬重,是对文明的服从。作为小说家,要去理解别人的愿望,但在对世界越来越没有把握时,在我们的知识已经非常丰沛时,就需要直觉,需要回到原始的本能,说不定会带给我们新的方向、新的路径、新的解决方法,乃至新的艺术,这也是“重逢准确的事实”中的应有之意。当你感到有点不知所云的时候,不妨模糊一下自己的概念,打破世俗生活中所制定的标准,可能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方式。把小说转化成一个通俗的艺术,有俗情,有理解,有情谊,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读到自己。
文化艺术报:这三年,受疫情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您的《掩面时分》《羊群过境》都触及了这场群体灾难,您的写作有没有受到影响?
弋舟:我们的生活都受到了全面的影响,写作当然也不能幸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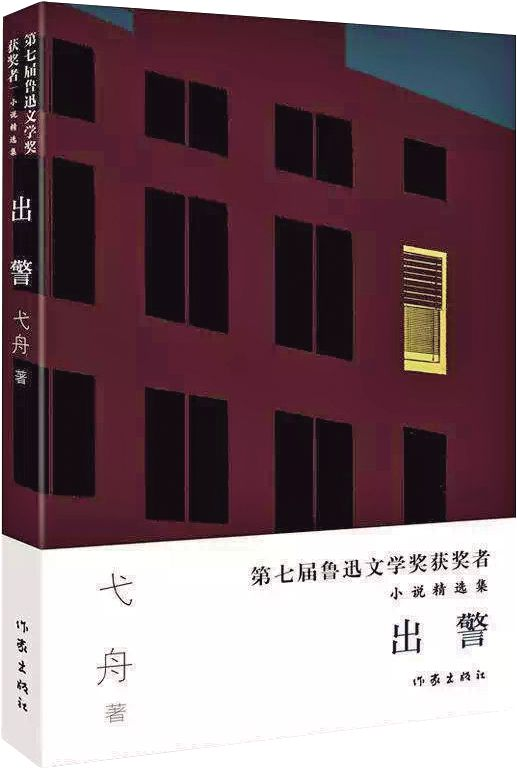
文化艺术报:非虚构作品《空巢》关注当下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原因让您写了这样一部非虚构作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孤独”作为这部作品的核心?
弋舟:首先它是个任务,出版社布置了作业,我得完成;其次,作为一个以虚构为志业的人,“缺什么补什么”,我需要有一些“非虚构”的平衡;再次,老人问题,更加关乎“生命”这样的议题,我需要更为聚精会神地凝望生命。
一直以来,孤独是我写小说时格外关注的一个角落、一个向度。为什么写这本书时格外突出它,不仅仅源于我个人遥望这个世界的方法,更基于空巢老人客观的生存事实。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空巢老人”这一社会现象也和改革历程有关。四十年前社会上也有空巢老人,他们更多受困于具体的物质生活的艰难。但今天走近他们,我们会发现物质问题已经不是首要的核心的问题,他们更多陷入了精神上的困境,这个困境的核心就是孤独。
如果我们去想象社会上的空巢老人,你可能觉得“他们只要健健康康、不愁吃穿,那问题就不大”,但问题是,一个个苍老的心灵,常常被我们忽视与罔顾。你会发现生命进程有这么一个规律,人是渐渐走向生命收缩的状态。随着岁月流逝,人的社会属性、社会身份在收缩。我们现在出门,貌似和谁都是朋友,可以干无穷无尽的活,我们能和他人发生密切的交织,但是衰老的根本方向是人和社会的交织在减少,这是所有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要面临的精神困境。有的老人还保有行动能力,但是社会不带他玩了,他的心理落差会更大。
文化艺术报:当时采访这些独居老人时,您带上了13岁的儿子。他能理解老人说的这些吗?
弋舟:这个生命事实对于那个年龄的孩子确实沉重。但既然是人类的基本生命事实,我们需要过多蒙住孩子的眼睛吗?
在我的观察里,一个孩子参与了成人世界的工作,他也有兴奋感。一开始他的理解可能达不到,但渐渐他听进去了,他对一些老人的态度,甚至自己的神情,都有了变化。我觉得他并没有被生命的严酷蒙上阴影,他在那样一个阶段表露出某种我愿意看到的一个男孩应有的镇定。
我也给他布置了任务,就是先把我们的采访录音整理一遍,做个筛选。他做得挺好。这份任务也有我的私心在,我想它既是一场情感教育,又能培养孩子的逻辑能力。
克服缺陷是无望的过程,但是你要去做。这就是价值和意义所在。

文化艺术报:鲁奖作品《出警》写到了老年人的孤独;《空巢》这本非虚构作品,再次面对这个问题。之前看到您是被当时的一段新闻触动,之后才有了与多位空巢老人之间的访谈。这本书出来引起众多媒体关注,之后,您好像再也没有写过这个题材了。
弋舟:每一个阶段会有不同的书写主题,但如果我们承认生命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事实,我们就得承认,自己写下的每一笔,其实都是在书写着同样的主题。
文化艺术报:在您的文学生涯中,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比较大?
弋舟:那是一条漫长的谱系,我实在难以只认《红楼梦》而不追溯《诗经》,只认曹雪芹而无视卡夫卡。但一个人的阅读脉络还是有迹可循的。我的父母都是学中文的,从小家里就不缺书,并且以古代汉语方面的书籍居多。小学阶段我囫囵吞枣地读了《史记》,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下背诵《唐诗三百首》,这些可能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影响,司马迁和李白,当然可能已经对我起到了教化作用。
由于住在大学校园,图书馆的存在给我带来很大的阅读便利,少年时期开始自发地阅读,我的兴趣就转移到了西方现代小说上,马尔克斯和大仲马带给人的震撼是不同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那时就学会了区别他们的不同。
还要说到的是我对当代文学期刊的阅读,这也要拜图书馆所赐,我对小说这门艺术萌生出操练之心,完全要归功于对文学期刊的阅读。很奇怪,少年时期的我捧着一本书时的心情总是近乎“瞻仰”,而捧着一本刊物,竟能生出跃跃欲试的冲动。
文化艺术报:您祖籍江苏,在西安出生、成长,后来移居兰州,在兰州成家立业,成名之后又被挖来西安,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弋舟:“成名”“挖”,这些词我都不大适应。经历仅仅是个事实而已,我的经历必定影响我的创作,但我也难以格外强调自己经历的特殊性。
成长的过程是时间的踪迹,而对于时间的敏感,在我看来算是一个好作家根本的能力。如果要我细数启发过我的作家和作品,我会发现,原来都能以“时间”的名义确立——《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不折不扣的成长小说,它写成长,写时间,《红楼梦》何尝不是呢?同样是写成长与时间,甚至《西游记》也可作如是观——一只猴子的成长史。当代作家中的余华写过《在细雨中呼喊》,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这部作品就刺激过我的文学冲动。
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着过不完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不仅是人生的,也是文学的。
文化艺术报:对一个很早成名的作家来说,您有没有什么缺憾?
弋舟:如果自己还算有点文学成就的话,母亲没能看到。母亲是一个特别有文学愿望的人,自己也搞创作,但是没能实现文学梦。她多少会对我有些期许,最后我当了作家也有回报母亲的愿望这点儿意思在。她给我推荐的那些,我开始看不上了;我给她推荐的,比如余华的《活着》,就特别能打动她。那不是我想在文学中提供给世界的。如果我的作品有这样的观感,那是我的写作能力和目的没能一致,我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就像我这个人,即使有消极或厌弃,还是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善意对待世界。对于西北,它似乎真的足以平衡我的一些委屈,让我得偿那些以往被自己视为陈词滥调的阔大与苍凉。西部这块疆域,不但是指地理意义,更是指精神领地。一个中国作家,有了这种大的参考,更有益于学会视自己为草芥。
文化艺术报:在长篇小说独霸文坛的今天,您的关注度都在短篇小说,好像在长篇小说上没有特别地用力,有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
弋舟:我也关注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
文化艺术报:如果不当小说家了,您想干什么?
弋舟:开个蛋糕店吧,或者做个体力劳动者。实在不想干精神的活儿了。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小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