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初读红柯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总觉得有一种迷狂,夹杂着冰彻心扉的悲哀和滚烫的焦灼,这部小说就好像一个发了高烧的人,不断地喊着“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个人是红柯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意象,夸父。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夸父死而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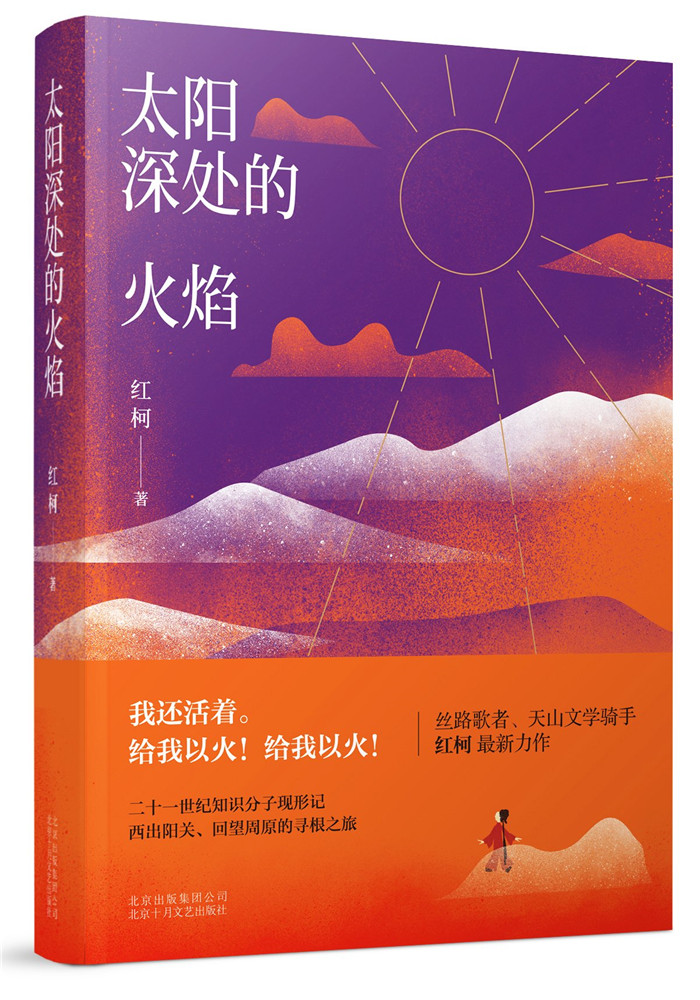
初读红柯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总觉得有一种迷狂,夹杂着冰彻心扉的悲哀和滚烫的焦灼,这部小说就好像一个发了高烧的人,不断地喊着“给我以火,给我以火”,这个人是红柯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意象,夸父。这部小说写的就是夸父死而复生。小说似乎是来自夸父的梦境与呓语,“太阳说:来,朝前走!”红柯所热爱的诗人昌耀就以他纵身一跃的决绝完成了自身对太阳的向往,还有海子,他们如此相像,在诗人的生命结构中神圣与世俗不可弥合,他们的人生都表现出了对于超越性精神的执著和对世俗生活的拒绝。红柯早期的小说也折射出了同样的二元对立,只不过是通过新疆与内地两种文化地理空间来表现的,这一点评论界都注意到了。但是,红柯从《生命树》《喀拉布风暴》《少女萨吾尔登》到这部《太阳深处的火焰》所展现出的对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评论界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不认为红柯的这种努力是为“一带一路”政策做注解,因为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就具备了这样的视野和气度,甚至他本人远走新疆十年,亲身实践了他的多元一体文化观和深受萨满文化影响的生命观。在小说之外的文字和言语间,红柯提起西域乃至中亚的民族来,对其文化和文学都是如数家珍般熟悉,若有机会他总会向别人分享他在汉文化圈之外的文化里所体验到的开阔与狂喜。对此他有一种狂热,曾经一度狂热地自学蒙古语。这在汉族作家里是非常少见的。
1999年由李敬泽、陈晓明、白烨、贺绍俊、李星等文学评论家召开的“回眸西部的阳光草原──红柯作品研讨会”距今十八年过去了,西部的阳光依然照耀着他,引导他走向太阳深处,太阳深处的火焰就是灵魂不死的火焰。《太阳深处的火焰》主要是通过吴丽梅与徐济云的爱情关系,通过双方的精神对话展开的。两人因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吴丽梅来自西域罗布荒原,而徐济云来自陕西关中,作家用了不少笔墨来表现两人生长的文化背景有多么不同:吴丽梅所生活的罗布荒原的山川草木、父亲母亲如此不同于徐济云的家乡,吴丽梅的清洁工母亲和泥瓦匠父亲就像高贵的艺术大师,毫无中原底层劳动者的卑微之感。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经由恋爱关系发生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对话。小说的叙事结构也许可以简单分为两种人物关系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吴丽梅和徐济云的具有“异类婚配”原型的爱情发展模式,第二种是徐济云与王莉与周猴、王勇、张林等等人物交织在一起的围绕“权力”(或利益)的依附关系发展模式。在第二种模式里红柯非常巧妙地使用了皮影艺术表演的手法来处理人物关系,使小说隐含了一个“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徐济云就是那个幕后的操控者、皮影表演者,而周猴(谐音肘猴)就是一个活皮影,王勇张林其实都是想成为徐济云的徐济云们。吴丽梅始终是置身“戏”外的观察者、反思者,也因此她和徐济云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的互为镜像的对话关系。整部小说采用第三人称视角,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展现了故事的背景与人物,而人物视角则展现的是人物的深层心理。耐人寻味的是这部小说所散发出来的叙事语气、叙事视角看徐济云们的生活时就像在看戏,充满了冷静的反讽,而转向吴丽梅的时候就转而成为了认同与仰慕。整部小说的情感在两者中间形成强大的张力,对前者越鄙视就对后者越热爱,两种精神境界之间的冲突与寻求对话的渴望是推动这部小说的根本动力。
小说里这对恋人之间的对话不似一般人的你侬我侬,而是谈学论道,如此这般:“你就想想几万年前几十万年前大风掀起一座座黄土山脉,鲲鹏展翅九万里,扶摇直上,沿塔里木河潜行万里从巴颜喀拉山再次起飞,沿黄河呼啸而下,构建起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黄土平原。”对此,文学批评家贺绍俊先生眼光毒辣,他看出了这部小说独特的复调结构,吴丽梅代表了新疆,徐济云代表了陕西,这两个人物一直活在红柯的内心,也一直处在对话的状态中,他们对话的成果便是红柯一部接一部的小说。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才会这样急于去表达自己,即使在恋爱中也急于在时间和空间的无垠里给自己定位?那就是在“文化震惊”的情况下。文化震惊,英文Culture Shock,指的是某一种文化中的人初次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模式时所产生的思想上的震惊与心理上的压力。在这场对话中主要是吴丽梅在表达,不管是她说给徐济云的话,还是她的思考她的学术论文,一直都围绕着两种不同文化所带来的“文化震惊”而反复表达,以至于她要绕开身体而穿越在精神的虚空里,对于少女吴丽梅来说恋爱中结合需要消弭的不是两性差异不是身体障碍,而是精神的鸿沟。小说里他们的性爱最终败于精神因素。这也是徐济云最痛苦的回忆。少女吴丽梅是怎样爱上徐济云的呢?也许是缘于边地人对中心的美好想象,而徐济云只是恰好出现,又或者是徐济云式的人善于捕捉人心幽微,城府太深,少女天真单纯,初到内地就失足掉了进去。短暂的精神对话结束后,少女毅然选择分手,远走西域进行长达一生的自我救赎。就此而言,红柯关于陕西和新疆的对话以及表达焦虑,就源于作家本人所体验的“文化震惊”。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碰撞带给人的心理震惊感已经减弱,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西方文化早已习以为常了。有人可能要问了,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震惊”难道要比中西文化之间的更大?听着似乎不可能,这也是红柯的“文化震惊”经验书写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的关键所在,其根本原因就是长期的汉文化中心所形成的文化心理,我们大多数汉族人不太了解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的文化自信和心理安全建立在我们有意识地不去面对。而吴丽梅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就使得她的恋爱也要背负比一般人更大的压力。为什么不是徐济云出现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呢?因为他身后的精神土壤实在太过于宽广,他直挂风帆济沧海,春风得意,这正是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所称道的那种成功人士,他拥有很多傲人的头衔,二级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因此可以说吴丽梅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和对自身文化夸父逐日一般地悲壮追寻,正是红柯流出热血文字的那个伤口。
张承志说:“我凭创造者的美意,一步闯入了新疆。虽然只有一些单薄寒碜的文字,但是我半生讴歌了——对他者的爱。是的,他者的尊严、他者的原则、他者的文明。因为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对他者的尊重。是的,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与清洁的皈依。我的文学,在新疆完成了人道与美的奠基。此刻我心里涌动着对新疆的感激。只有我清楚这感激有多深沉。”和张承志一样,红柯也用半生讴歌了对他者的爱,对他者隐痛的感同身受,这无疑是一种超越了同时代作家的文化视野。
新疆何以有这样大的魅力,让每一个倾心探听的作家发生改变,给予成全。除了张承志、红柯,这个名单上还有王蒙、周涛、刘亮程、李娟等等很多人。这显然是因为它独特的文化。也因此吴丽梅一路追着太阳赶回新疆在小说里成了一个象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比起徐济云的立体丰满形象,吴丽梅像一种精神之火,像阳光,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徐济云的阴暗生活被看见。或者可以理解成吴丽梅就像是青年徐济云生命之火的瞬间光亮,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经由爱情点燃,忽而一闪,成了一个想象,一场梦。神话学家坎贝尔说:“神话是众人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吴丽梅便是那梦中女子,具有了神话的色彩,吴丽梅的学术研究,吴丽梅的家庭生活,吴丽梅的精神向往都变成了一种神圣化的存在,而这正是这部小说的力量所在。因为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角,虽然是第三人称视角,可是它是一种世俗的有限视角,并非全知全能,一切皆可洞悉。这种视角去观察吴丽梅的时候,在仰望,在远观,被召唤,吴丽梅似乎变成了太阳的一部分,而叙述者成了夸父。还是同样的叙述者,当它的叙述视角看向周猴、徐济云的生活时则是冷静的、悲悯的。因此这部小说除了上述的表层叙事结构之外,还隐含着一个深层的象征结构,那就是夸父逐日而死的神话。《太阳深处的火焰》这部小说正是通过吴丽梅展现了这种英雄主义精神与水火交融、阴阳和合的天道。徐济云最后听从内心呼唤,登上飞机,融入蓝天。第三人称视角呈现出来的是作家的眼光和内心世界,可见写作于红柯而言也是他超越神圣与世俗二元对立的救赎。
这部小说总体而言是一部21世纪知识分子现形记,和一般作家的揭露批判不同,红柯写知识分子除了写人与人的关系,还写人与天地,人与天道的关系,所有一切在他的小说里都是一个整体。这种小说写作手法与他深深认同的萨满文化的生命观,与他多元一体的文化观密切相关。当下不少赶“丝绸之路”热潮的作家恐怕还没有搞清楚丝绸之路到底意味着什么,红柯却说,“丝绸之路完全是太阳喷射的火焰”。 太阳说:来,朝前走。
【作者系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编辑:阿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