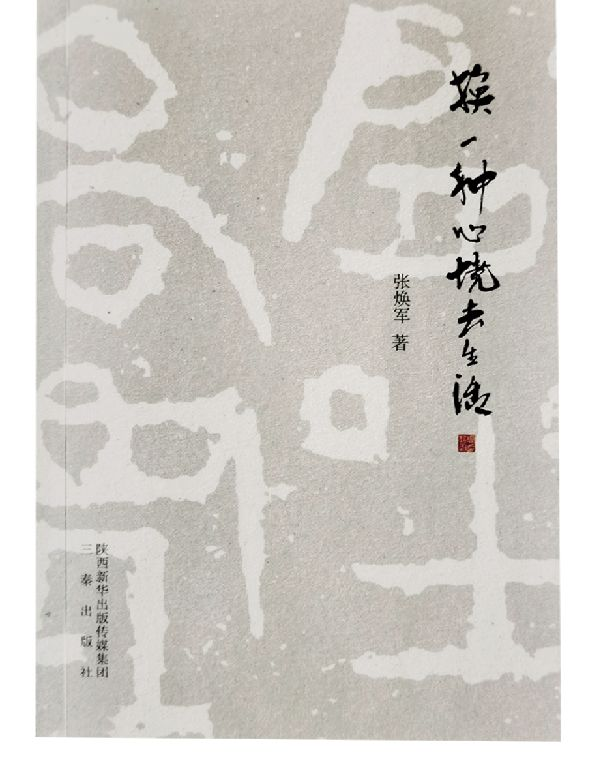
张焕军的散文,每一篇的入口都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比如一株花,一次拜会,一条短信,一回交谈,一缕回忆等,但诸如此类,却都能化为策动他提笔作文的号角。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气氛的渲染,没有故弄的玄虚,没有忸怩的作态,家常得恍若邻居间的路遇闲聊,随意得仿佛漫不经心的导游在向牧羊般散漫的游客拉闲散闷。然而神奇之处在于,读者一旦尾随他的笔头从洞口进入,并巡游其间,就会恍然发现阔大的洞内,竟如此深不可测,如此蕴藏丰富,仿佛一座琳琅满目的仓库那般殷实厚实。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呈现出的格局是,头小身子大,头低尾巴翘,用民间惯用的熟语来比喻,就是小牛拉大车——更为精彩的演绎,时常藏于其腹,躲于身后。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通过研读不难看出,张焕军不但是一个生活的重新发现者,是一个把生活的简易“食材”烹饪成散文般丰盛“佳肴”的高超的“厨师”,而且是一个不懈的捡拾者和思考者。他的“食材”,不是现成的,不是码放整齐的,而是混淆于其他杂物之中,是零散而零碎的,全有赖于他独具慧眼的捕捉与身手敏捷的擒拿。他流连于往昔,寻迹于现实,关注人与现实共生而又敌对的关系,忧患世风的走向和生命的处境,并力图破解状态各异的个体之所以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性基因和精神密码,并在不断地条分缕析中,融入自我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原本很微小的事物,很普通的经历,经他像拉拉面和烤面包一般地延伸和拓展,就不再微小,亦不复普通,从而化苗为树,并使树有了蓬勃的枝丫;化水为河,并使河有了翻卷的浪花;化僵硬的文字为楚楚动人的有情之物,使文字在具有肌肤之热的同时,更具有思想的内蕴和艺术的光华。
他从“那盆君子兰”的花开花谢,提炼出“任何东西都是需要呵护的,你亲近它、照顾它,它就会回报你,给你愉悦”;从“桂花的淡然”中,推而广之出“人是应该向植物学习的,不畏风雨吹打,不惧雷电交加,生存一天,就活出自己的性情”;从妻子“在为窗外的天气发愁”里,节外生枝出“春天不光有花朵,还有春愁”……诸如此类,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如此这般的延展与感悟,不但促使题材超越题材本身的局限,而且促成题材从蛹到蝶、从虫到龙、从丑小鸭到白天鹅以及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进发、嬗变与提升。这样的演化过程,是散文质量从根本意义上的一次次超度和飞跃。
张焕军的散文另一个难能可贵的特性在于他对人的守望与不舍不弃。人既是他散文的书写对象,亦是他散文的核心要素,更是他散文的价值目标。他写女儿,一个父亲的慈祥与疼爱,跃然笔端;他写妻子、写父亲,在轻描淡写中蕴含着滚烫之爱与浓烈之情;他写朋友、写师长,在一鳞半爪的细节里,让人的面目呼之欲出。甚至,他写植物、写动物、写山川,都能将其当作平等的生命体来尊重和怜惜,没有居高临下的睥睨,有的是羊羔跪乳的感恩情怀。
散文,包括文学,甚至包括更大范畴的社会与世界,都一定与人有关。人一经缺席,文学不复为文学,社会不复为社会,世界存在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散文是关乎人的文体,人是散文的主角,亦是散文的命脉。人的喜怒哀乐,人的油盐酱醋,人的白日做梦,人的命运沉浮,无一不是散文守望和狩猎的对象。即使是那些看起来非人的客观存在,却唯有与人建立起关联,才能赋予其自身的价值坐标,比如白昼的太阳给人以照耀,夜晚的月亮给人以遐思,植物给人以优化的环境,动物让人不再孤单,桌椅给人以方便,房舍给人以家园……从人的本体出发,又回归于人,抵达于人,滋补于人心,潜移默化于人的魂魄——这正是张焕军散文的优长之所在。
文字是有气质的,甚至是有味道的。有的文字如麻辣烫,味道浓郁;有的文字如三鲜汤,味道清淡;有的文字如酒,辣得人皱眉;有的文字如茶,饮得人清爽……张焕军的散文,无疑属于后者,弥散着茶的清香,流荡着云的散漫。但清淡不等于寡淡,散漫不等于涣散。他的文字,在茶中添加了用于施救的中药,在云中注入了动辄就金鞭舞动的闪电,因此香中隐含苦,散而不轻佻。
整体而言,张焕军的散文是质朴的,也是无雕无琢的,像不施粉黛的村姑,更像朴实无华的泥土,但在泥土之上,却是姹紫嫣红,龙飞凤舞,云蒸霞蔚。泥土是他文字的质地,而云霞是他散文的精魂——他用大众听得懂的平实话语,不慌不忙而又娓娓道来地在劝世、在陈述、在倾诉、在追忆,在抒发人间之爱、在阐述益世之理。
编辑:慕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