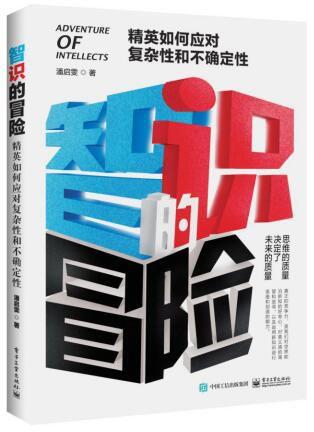
《智识的冒险:精英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潘启雯/著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如何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或特征: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从哲学角度一直被称为“冒险时代”;17世纪的“理性时代”过去之后,“启蒙时代”随之而来;19世纪和20世纪则分别是“意识形态时代”和“分析时代”;至于21世纪,全球的时代特征被众多学者概括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说风行学界,原因有两个。其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可以创造生命,甚至通过极其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制造新物种。以色列历史学家、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里预言人类即将可以“扮演上帝”: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操纵自然,包括推迟甚至最终征服死亡的可能。美国相关机构所认定的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关键技术趋势在30年前都还闻所未闻。其二,人性被无望和沮丧感重重包围,这些感觉来自我们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污染、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人工智能、自动化、共享经济等导致的就业岗位消失、对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具破坏性的争斗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大大加深了我们的无力感。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界,从而指导我们为推动和平与繁荣做出努力。当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两个重要社会趋势的存在,也让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以及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行的“智识”(智慧和见识)上的冒险。
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
复杂性,即科学家通常所说的“复杂系统”,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实上,复杂系统早在30多亿年前就出现了。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便是一个复杂系统,蚁群、地球气候、老鼠的大脑、一切活细胞内的生物化学过程皆是如此。此外,还有人为的复杂系统,即人类无意识地干预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如气候。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制造了气候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一点。
“复杂性范式”是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1973年发表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首先提出的概念。1979年,比利时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也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口号。莫兰认为,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认识是在承认对象的多样性因素之后,还看到对象的统一性因素,即把对象看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有序性和无序性的共存使得事物和主体本身常常面临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关于复杂系统,南非学者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在《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Complexity & Postmodernism :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一书中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了它的10项本质特征。
(1)复杂系统由大量要素构成。当要素数目相对较小时,要素的行为往往能够以常规的术语赋予正式描述。不过,当要素数目变得充分大时,常规的手段(例如某个微分方程组)不仅变得不现实,而且也无助于对系统的任何理解。
(2)大量要素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并没有兴趣将沙滩上的沙粒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要构成一个复杂系统,要素之间必须相互作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必定是动力学的。一个复杂系统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相互作用,不一定必须是物理的,也可以设想成信息的转移。
(3)相互作用是相当丰富的,即系统中的任何要素都在影响若干其他要素,并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不过,系统的行为,并不是由与特定要素相联系的相互作用的精确数量所决定。如果系统中有足够的要素(其中一定有一些冗余要素),若干稀疏关联的要素也能够发挥与丰富关联的要素相同的功能。
(4)相互作用自身具有若干重要的特征。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线性要素的大系统通常会崩溃成小许多的与之相当的系统。非线性也保证了小原因可能导致大结果,反之亦然。这是复杂性的一个先决条件。
(5)相互作用常常作用于某个相对小的短程范围,即主要是从直接相邻处接收信息。长程相互作用并非不可能,但是实践上的制约迫使我们只能做这种考虑。这并不预先排除大范围的影响——因为相互作用是丰富的,从一个要素到任何另一个要素的途径通常包含着若干步骤。结果是,相应的影响也按此方式进行了调整。这可以通过若干方式得以增强、抑制或转换。
(6)相互作用之间形成回路。任何活动的效应都可以反馈到其自身,有时是直接的,有时要经过一些干预阶段(intervening stages)。这样的反馈可以是正反馈(加强,激发),也可以是负反馈(减低,抑制),两种反馈都是必要的。在复杂系统中相应的术语叫作归复(recurrence)。
(7)复杂系统通常是开放系统,即它们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事实上,要界定复杂系统的边界往往是困难的。系统的范围并非系统自身的特征,而常常由对系统的描述目标所决定,因而往往受到观察者位置的影响。这个过程被称作构架(framing)。封闭系统通常都只是复合的。
(8)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因此必须有连续不断的能量流,保持系统的逐级传递,并保证其存活。平衡不过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
(9)复杂系统具有历史,它们不仅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
(10)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对于整体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它仅仅对其可以获得的局域信息做出响应。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某一要素对于作为整体的系统将要发生什么都“知道”,那么所有的复杂性都必定出现在那一要素中,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复杂性是简单要素的频繁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简单要素仅仅对呈现给它的有限的信息做出响应。当我们观察作为整体的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系统的个别要素转移到了系统的复杂结构。复杂性正是由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从“复杂系统”这10项本质特征中不难发现,复杂系统是到处存在的,并不是只有社会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每个原子也是复杂的。
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说过一句话:“世间的阴差阳错从未停歇,都是寻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世界及未来的种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颇为贴切。早在1969年,如今常被人们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就预言,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连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市场、商业运营,甚至工作的本质都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这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他的畅销巨著《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中延续了德鲁克的这一思想。托夫勒将未来描绘成一个不断经历冲击的社会,因为“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组织机构教育专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在1973年的著作《超越稳定状态》(Beyond the Stable State)中甚至认为,我们的社会将永远不可能复归稳定。基于这一点,舍恩提出,企业必须将自己定位成不断学习的组织机构。
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了“变化加速”这个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这种现象称为“现代性”的晚期阶段。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技术和企业,就连社会结构本身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理念深深地影响并成就了之后的一大批商业类书籍作家,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彼得斯和哈默尔甚至将“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本身变成了一门管理学的新学科。
人们不禁要问:“变化”真的有那么耸人听闻吗?上述诸位思想家的理论固然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论点放到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来检验。正所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但是并非所有变化都是大地震。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分清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第一种是那些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不确定性”,第二种则是在大的文化变迁下的“不确定性”。
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家按照复杂程度来区分这两种“不确定性”: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总是看似简单,解决方法现成就有 ;但渐渐地,它越变越复杂,越变越看似无解。
与《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提出的“复杂性范式”概念相映成趣,莫兰在《教育的七个黑洞》中则认为:“人们教授确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确定性。”他这样描述学习:“我们被迫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时而穿行于确定的群岛之间,这就是人类的冒险。今天,我们知道这是未知的冒险,我们需要一种教育,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冒险而不气馁。”其强调的是教育不应该只关注一些确切的知识,一定要正视不确定性。就科学教学而言,在自主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结果出现一些不确定,也许更贴近真实的探究学习的状态。多一些这样的经历,会让学生从小就明白,很多事都不那么确定。
按《反脆弱》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特聘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说法,对于不确定性,你要利用它,而不是躲避它。也就是说,决策要从不确定性中获取收益。
思维的质量决定了未来的质量,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精英们又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呢?
复利既出乎意料又是危险的
假设你把1000美元放在免税账户里,这笔投资每年有7%的回报率,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原始投资翻一番?
A.0至5年
B.5至15年
C.15到45年
D.45年以上
这看起来像是一道数学题,其实不是。你既不需要知道怎样计算,也不需要知道所谓的“72法则”,而是考验你对复利的直观理解。具有这种金融知识的人知道,按照现实的投资回报率,把钱翻一番大概要花10年时间。这意味着正确答案必然是B。
人类努力的成果是按算术法则累积的:1、2、3、4、5、6……过一天,多一元钱。 债务和投资与此不同,它们的累积遵循几何法则:1、2、4、8、16、32……这意味着,复利胜过纯粹的体力。财富总流向那些能让复利为己所用的人。
按照《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分析,复利是收入不平等的基础。富人(精英)因为投资会更加富裕,普通人的工资涨幅根本赶不上复利。“复利的力量”是现实世界几乎所有财务建议的潜在公理。在当今疯狂信贷的社会里,资本不足的人一拿到薪水就会花个精光,他们为买车接受疯狂的贷款利息,彻底透支信用卡额度,艰难地偿还学生贷款,还要按揭昂贵的抵押房贷。复利让穷人变得更穷。这就是为什么财务规划师会建议,你要尽早开始储蓄。从21岁就开始存钱的工人,靠投资回报赚到的钱可能比自己一辈子的总工资还高。复利是所有可观财富的基础。成功的企业家并不比其他人努力一万倍。相反,他们找到了一种指数型发展业务的方法,只要短短几年就足够了。
一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赏,是在棋盘的第一格里放一粒米,以后每一格中的米粒数都比前一格增加一倍,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以为这奖赏微不足道,但是算到第21格的时候,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万粒……到第41格时,已经超过了1万亿粒,而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满这一格了。故事的结尾是,据说国王因为觉得自己被骗而愤怒不已,砍了国际象棋发明者的头。这充分说明了复利刁钻微妙的性质,告诉人们复利的隐匿力量很容易被低估。
当然,复利也是危险的。住在伦敦的德鲁森,一位富裕的瑞士商人与银行家,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能保持7.5% 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900万英镑(远超英国当时的国债),届时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代。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1800年通过法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后代对该法案提出异议。经过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最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产。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便是以此为蓝本。
一些研究暗示,经济安全感解释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相关性。高收入本身不能带来安全感,“月光族”会担心失去一切,有些节俭的教师和警察有一笔储蓄作为风险缓冲,使自己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获得安全保障。财务行为也能反映出和幸福感有关的性格习惯。能控制支出并设法存钱或投资的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然而,控制支出就像是“棉花糖实验”。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曾做了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米歇尔给一群4~6岁的孩子一个“恶毒的”选择 :每个孩子都会获得一块棉花糖,他们可以立即吃掉,也可以忍耐15分钟再吃,届时就可以再得到一块棉花糖作为奖励,而且在这折磨人的15分钟里,第一块棉花糖就在孩子们的视线中,触手可及。
一些孩子马上把棉花糖塞进嘴里,另一些孩子则陷入了哈姆雷特般的纠结,进退两难。有的孩子玩起了“奥德修斯和棉花糖”游戏,蒙起眼睛转过身,背对着棉花糖,躲避甜美的诱惑。
米歇尔用秒表为孩子们计时,孩子们屈服于诱惑的平均时间是6分钟。米歇尔的女儿就在“棉花糖实验”最初施行的学校上学。随着时间的流逝,米歇尔和女儿注意到,立即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和那些能抵挡住诱惑的孩子之间出现了差别:后者在日后的生活里更成功。他们的成绩更好,升入了更好的学校。他们似乎更快乐,没那么多烦恼。
没熬过15分钟就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往往在学校和人际关系里表现不佳,会出现更多跟酒精和毒品相关的问题。米歇尔和同事们开始对最初的“棉花糖实验”进行后续研究。他们发现,孩子延迟吃棉花糖的时间(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跟日后生活成功的量化指标(如 SAT 分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越早吃糖的孩子,成年后患上肥胖、边缘人格障碍、服食可卡因和离婚的比例更高。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节食的人放弃吃糖带来的快感,不是为了几分钟后能吃两块糖这微不足道的回报,而是为了长久的健康、苗条和魅力。精打细算的人按捺住轻率的购物冲动,是为了存钱买新车,或是给孩子攒学费。关注健康的人忍受长期的剥夺感和不方便是为了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十年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没人说你总要延迟满足。在这方面,民间智慧讲得好:“人只活一辈子”“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关键是要能达成平衡。为什么有些人能更好地克制冲动进行长期规划,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那些努力掌握了这类能力的人有更大可能学习、记住与自身相关的特定事实,并将之内化于心。知道金钱利滚利的速度有多快就属于这类事实。复利跟物理学中的光速概念一样,是金融宇宙的基石之一。这种事不仅富人(精英)必须了解,还能激励普通人减少债务、积极储蓄。
了解一件并非切身相关的事实就是一次“棉花糖实验”。要获得不确定且会延迟的回报,人就一定要自律。长于自律的人更有可能精通有关财务的长期规划。
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或许是建立自律的好方法。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既需要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又需要打破范式、超越壁垒、补充新知和修正思维框架。
关于本书:“有意义、有意思”
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是一本说教的教材,也不是一本完备的行动指南。我既不可能在书中完整地介绍所有有用的知识,也不打算列举这些知识的目录。我还不能保证书中所说的一系列理论永远经得起新科技和时间的长久考验。但我保证书中所有内容都是“有意义、有意思”的。
“有意义”代表了移动时代(或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知识的主流价值观取向 ;“有意思”则表明了本书传递的思想适应现代人的阅读诉求,用新鲜的表达方式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新颖的案例进行辅助解读,以提高新知识、新思想的有效传播。
第一部分“错觉向左,平衡向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生活中各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状况,其实都暗藏着各种“错觉”。每当人们在开车时拿起手机,人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注意力资源会出现分配不足的状况,人们陷入了错觉;当有人错误地回忆了某件事时,人们总会认为他在说谎,人们陷入了错觉 ;那些表现得最有自信的人总能赢得人们的信任,人们陷入了错觉 ;当人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计划并认为绝对能够按时完成时,还是陷入了错觉。在玩扑克的人中间流行一句格言“长考必错”,所以《纽约客》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畅销书《决断两秒间》(Blink)中说,我们在做决定时应该相信直觉,迅速决断。他的论据是,进化心理学认为,我们已进化到能迅速地做出决定,进化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跟我们的大脑在进化时已经大为不同,比如物体移动得更快了。在我们的视觉系统和注意力进化的时候,我们还不会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时移动上百千米,所以那时我们不需要注意大量高速冲向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事物。其二,这一部分还介绍了高价值创造者(精英)是如何保持旧模式和新方法(或判断力和想象力)的融合及平衡的,另外人际冲突是如何发生的、男孩到男人是如何演化的等前沿研究。
无论是警惕错觉、不轻信直觉,还是保持“判断力和想象力”的平衡,那些看起来最合理的结论往往都是错的,通过解密人们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从而避免“理性”的推理蒙骗了自己。我期待这部分的内容帮助你绕开思维陷阱,抵御错误、可疑的观念,培育正确的思维习惯。因为知识为用,思考为本,一切知识显然都是应该为思考服务的。
第二部分“新技术和创造力”,结合复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进化心理学、脑科学等,聚焦于互联网思维、3D打印技术、众包、共享经济、摩尔定律、“超新星”、“出神状态”等新技术和创造力如何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过:“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由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许多职业会不会被机器取代呢?例如,家政工作者、银行柜员、服务员,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只要个人、企业和政府致力于终身学习,机器就不会抢走所有的工作饭碗,科技甚至会创造出更多新职缺。如何应对新技术和创造力背后的新原则,或许是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大法宝。
第三部分“经济学新思维”,主要关注技术分析和投资演变、破除“错误认识”、经济依赖和战争的关系、区块链等话题。尽管投资和商业确实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引擎,但是在现代文明之前,大部分个人并不能直接从这些活动中受益。相反,普通人还需要为推动历史和金融进步付出代价,劳动力不断受到剥削。无论是为借款人策划一份独一无二的协议,还是慧眼寻得一个有潜力的投资机会,抑或是精明地决定最优的资本结构,在各种各样的投资过程中,创新都居于核心地位。不难看出,成功的投资者所采取的创造性举措,最终不仅依赖于投资项目本身的创造性,更依赖于投资管理。虽然短中期或有种种不确定性,但这并非是最坏的时代,市场仍孕育着巨大机遇,从多维度审视“技术分析和投资演变”,或许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财富和未来生活。
第四部分“精英主导的时代”,在精英的世界里,无论是气候变化公约还是世界税收计划都带有很强的正当性,有利于逐步构建国际标准,从而符合某种秩序,或许最终秩序会使普通百姓察觉出奴役感,精英们的计划非常缓慢又掩人耳目,可谓煞费苦心。但当首选方法几乎无作用时,精英们想起了“冰9”,即锁定或冻结系统。
面对一只狮子,角马的防御要靠群体,一只角马绝不是一只狮子的对手。在横亘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上,黎明时的一只狮子走向角马群,它在选择攻击目标,然后冲向猎物。角马会齐心协力应对狮子,先是四散逃窜,扬起一片尘土,并不停改变方向,当狮子扑上来的时候却汇成一股,踩踏狮子逼它撤退。不过狮子很少会饿着回去,它最终会杀死一只角马,在阳光普照的原野上吞噬角马的肉,并骄傲地分享猎物。温热的鲜血从狮子的口边流下,从角马的角度来看,虽然损失一只很不幸,然而角马群幸存了下来。
塞伦盖蒂草原上的这个场面正体现了当下货币精英们的心态。货币精英就好像是角马群。他们不是一个阴暗的地下组织,而是特定的一群人——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学者、记者和智囊团。角马群同意市场是有效的,尽管有不完美之处。他们同意供给和需求会产生局部的均衡,而这些均衡的总和是一般均衡。当均衡遭到扰动时,可以通过政策来恢复。角马群同意浮动汇率会产生推动一般均衡的价格信号和市场反应。他们赞同自由贸易(这植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优化财富创造(尽管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他们同意黄金是野蛮人的遗留物。从“焦虑、合作和掠夺”等角度把脉政府的行动和制度设计,我们或许会发现,把权力和欲望关在笼子里,公共机构就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而不会欺压民众。
缺乏智识的人,除了难以发现自己的无知,还有可能失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移动知识时代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把握和利用前沿新知的方法,以保持对各种信息的洞察力,从而能更好地避免陷入“达克效应”的陷阱。并不是每个基于未来思考的人,都能在这个新的全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进退自如。但始终基于未来思考并保持“智识冒险”心态的人,得到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还会有很多乐趣。
编辑:高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