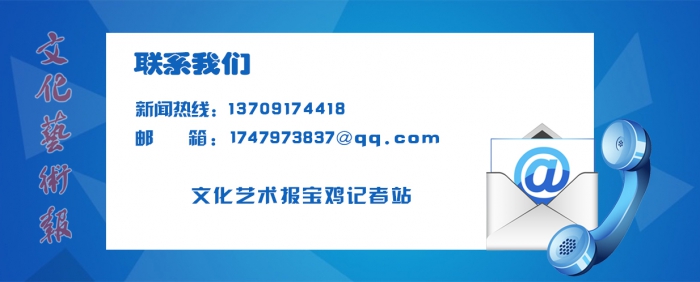一
1830年(道光十年)底,在那个信息传播闭塞的时代,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罗曰壁任汧(千)阳知县。
当时,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没几人在意这平常不过的任命。但直到近二百年后,回望历史,才真正感到,千阳有幸,百姓有幸。
这位知县,是云南景东县人。民国十一年《景东县志稿∙科举志》载:罗曰壁,嘉庆九年甲午科举人,任陕西蒲县知县。寥寥几个字就总结了这位官员的一生。后多方查史又知,清道光六年任延川知县,道光十年任平利知县,道光十年十二月任汧(千)阳知县。生卒不详,离千后去向不明。
罗曰壁到任后,已近春节。据说,他很勤勉,晨起迎着朝阳去百姓家、乡贤家走访,夕阳西下拖着长长的身影回到县衙,夜里查阅史料到很晚。
日复一日中,他由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山梁川塬,田畴阡陌,千水南北处处留下了一位朝廷命官的身影和足迹。他穿过一孔孔窑洞一贫如洗,见到一个个百姓衣衫褴褛。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出着最大的苦力连接着最低的收成,百姓除了反复折腾脚下的泥土,不知还有什么其它过日子的方式。罗曰璧越走脚步越沉重,越看他的心情越凄凉。
经过细细考察,对于千阳县情,他脑海中有了很清晰的认识:穷根深,文教薄,史料缺。
一个个寒气逼人的夜晚,孤灯下,脑子里全是白天看到的赤贫状、破败相,现状的触动对他更直接,因此他思考的更深刻、设想的更长远。他深知一个知县的行为和抉择,会反射到百姓身上。经过反复斟酌,终于理出了他质朴又具体的施政纲领:劝农桑,兴文教,编志书。于是他研墨取纸,提笔落字。一盏微弱的油灯,从此点亮起万家灯火。
这一张薄薄的白纸黑字,在罗曰壁看来,亦犹千水之湍、千山之重。他没有选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贪心之路,也没有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躺平之路,而是选择了每走一步都步履艰难的上坡之路。
为了他的十二字施政纲领尽早落地,他常常在衙门里处理完公务,脱掉官服,换上长衫便鞋走出县衙。县太爷的身份,一出县衙大门,就转变成了农技员、教育者和典史员。
二
罗曰壁走遍千阳,对农事得出结论:“千阳地域周围不过百里,析而言之,川一半,原一半,山一半。而川地半成沙滩,经淤务稻,一遇大水泛溢,往往有种无收;高原旱涝不匀,必收成欠薄;而山地更可知也”。他感慨到:“县人全赖农业以养室家,合计夏秋两收,尚多不足一年之食。”
进而他在村庄还见到一个普遍现象“农人逸坐冬春,不事劳作”。他认为“习为陋俗”。接着又追问“寒又从何而衣”?回答他的只剩田野的风声。
“寒又从何而衣”?走在单调的旷野中,在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呼啸声中,他缩脖裹紧棉衣,嘴里反复念叨着这句话。
很快有了答案:植桑养蚕。
因为他得知,千阳以前也曾有过植桑养蚕,那么证实这里的气候、土壤、雨量等资源禀赋非常适宜发展蚕业。只是土法喂养不得法,渐渐就放弃了。
于是,罗知县把“寒又从何而衣”的答案,全部倾注于笔尖,像极了他科举考试时的严肃样,自信满满的书写下去。当然,他也深知,他书写的就是试卷,而阅卷者将是千阳的养蚕者,分数就是植桑——养蚕---缫丝——织衣。
道光《重修千阳县志∙地理志卷一》中,记载了种桑子法、蚕桑法则等内容。用十多页的篇幅分类详叙,如何选种、育苗、移栽、株距、施肥、剪伐等过程做了一目了然的说明。对蚕室消毒通风要求,头眠二眠三眠四眠,眠、起间隔时间及不同喂养频次,制簇材料方法,除沙防潮,上簇结茧的观察法,烤茧时机,缫丝水温等等具体环节一一记之。
特别还提到,喂蚕时忌“湿叶、雾叶、干叶、黄沙叶、气水叶,臭气、香气、不洁净人、灯油气、酒醋气、葱韭蒜、硫磺等臭,堵塞鼠穴。”
这么详尽而又实用的植桑养蚕缫丝技术要领和注意事项,对于养过近十年蚕的我,最直接的感觉是罗知县栽过桑、养过蚕、缫过丝。
《景东县志》畜牧养殖业总论里记载:……“其它养殖业有养蜂和养蚕,不多”。分类叙述中再没有提到这两类。那么,他在家乡参与养蚕的可能性不大。
《平利县志》载,“道光六年(1826)任知县的司徒修,下村即劝民兴水利、广积储。梓《蚕桑须知》《树桑百益》等书散之民”。陕南的平利县,明朝洪武年间就有农桑记载,说明当地植桑养蚕的技术很成熟。
道光十年罗曰壁任平利知县,虽然任上不到一年,但他乐参与、好学习、善总结、再推广。离任赴千时,一定往行李中塞了几本《蚕桑须知》、《树桑百益》等梓书吧。
史料没有留下多少农户从事养蚕的记载,但罗曰璧任知县十年后,县志“物产·货类”中将“丝”放在了第一位,后面依次是“麻、羊绒、毡、酒、油、烟、皮革、石墨、石灰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千阳桑园面积达到6万多亩,川塬镇村几乎家家有桑园,户户在养蚕。家里养蚕卖茧供我上的学,近两百年后,阅卷者延续到我,作为受益者,打满分。
三
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有较成熟的公办学校,到了孔子,开创了私学的先河。公元前506年,燕伋二次从曲阜返千后创办了渔阳塾坛。这足以说明偏于一隅的千阳,重文兴教起步极早。
那天,当罗曰壁来到三贤祠(今城关镇政府驻地)前,未曾开口,心却被入眼的一幕狠狠的扎了一下。明末附设于此处的隃麋书院,本就狭小简陋,此时更是残破不堪,徒具虚名。跟随的衙役,都能感觉到那一天的空气异常压抑。
渔阳塾坛太久远,可能因改朝换代的战火而未能延续下去。隃麋书院,明显是因经济上的入不敷出使它陷于困顿。
夜晚,在油灯的映照下,满脸愁苦的他只想着一个字:钱。
作为知县,他清楚的知道,全县田赋、税收、附加等各项年征银5565.411两(额定数),上解近一半,留下的要支付29项之多,全是俸银和夫马工料银等。这个数字,他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也就是说,支过人头费和马头费,不剩一点银两。即便是风调雨顺的年间,连修修补补的多余银两都没有,还奢望新建书院?
前任知县,前任的前任,可能都曾想过为书院添砖加瓦,可一提到银子,又不得不照旧了。缺银,真正难倒了知县大人。
熟读史书的他记着大理学家朱熹的话:人性皆善,步入社会后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两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从根本、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
他坚信“学校关乎风化,乃为政之大端”,在千难万难中,兴文教的决心始终未变。大手笔的他不想在旧书院上缝缝补补,他要建新书院。务实的他,很快选址在城东北的旧察院。
1837年(道光十七年),新书院破土动工。他任知县七年后才付诸实施,我想,拖着的原因还是缺银。等了几年也没有多余的银两,他捐出了自己的养廉银。清知县的俸薪很低,千阳知县俸薪银23.7两,但养廉银有600两。
他在《创修千阳县考棚碑记》中说:“千小邑也,纳税不过五千,而童试则四百有余,历试数次,搭盖席棚以为考场。匪特风雨堪虞,亦且关防难密,殊属不成事体”。以席搭考棚,他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书院历两年竣工,取了个很有文化的名字,启文。
书院的平面图,我须用敬仰的眼神凝望。整体呈长方形,格局新颖,设施齐备。大门三个,中间称之龙门,左右两开,龙门只在开考时打开,大门前植梧桐二株。龙门至后堂,中间一条甬道,以条石、青砖铺之。以甬道为中轴线,对称结构建筑,分前后两院。建有客厅、讲堂、考棚(童试教室)、书房(图书馆)、碑房(档案馆)、宿舍、厨房、门房等五十多间。
这里只细说一个建筑,两院相连的月台,宽二丈、长四丈六尺,外砌青石条。
书院建成后,罗曰壁邀请时任凤翔知府的豫泰撰写碑文。“泰骤闻而讶”。知府大人惊讶的是,罗曰壁怎么就悄无声息在这么穷的小县,干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呢!
罗曰璧聘用比较著名的学者执掌校务,叫“山长”。称呼应该是承袭来的,如古代创办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选址于名山胜景,负责人就叫“山长”。
罗曰璧添置《圣谕广训》、《朱子全书》、《十三经全书》、《二十一史全书》、《明史全书》等典籍于书房,供学生阅读。
为书院长远考虑,罗曰璧每年将狼牙洼、赵家河、普门寺等处地亩收的租钱用于书院开支,铺面出租钱用于后期维修。又将学田的亩数、界址存立县案,永为查据。
如此有力的举措接二连三的出台,启文书院显现出一派繁荣。所收生徒分编两班,每班有时达六七十人。清代后期千阳人才茂兴,归功启文书院。
180多年前,从悬挂启文书院的牌匾起,启文之名就成了罗曰壁之新名,这个新名将长久的在千阳延续下去。
今天,走过启文巷,清晨入耳的是孩子们清脆而嘹亮的读书声。细听,那是对他的赞歌。
四
千阳这片大地,人类居住史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自汉置隃麋县始,历经晋、隋、唐、宋、元、明等朝代更迭,至清朝前,已有一千多年的建县史。
然而,直到1650年(清顺治七年),来千任知县的江都进士王国玮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凡郡邑都有志,千独无志。”
响彻在千阳上空的这一声疑问,直到今天,仍在文史者的口中常常听到,但没人能给出足够信服的答案。
1731年(雍正九年),任千阳知县的江南武进监生管旆下车即索志,“始知千之志于明季兵燹之后已散轶而不可考”。这是旧志史料记载上,唯一对王国玮之问的回答。
我认为有可能。因为古代千阳这片土地在较长时期,处在西北少数名族割据政权与中原政权的交叉区和军事拉锯地。在一个相对和平时期,是无足轻重朝堂不在意的疆土,而一旦狼烟四起,又是双方军队往返路过时的歇脚之地,也可能是大小战场之处。
明朝后期,社会震荡,对城镇杀戮、掠夺、烧毁无数次的反复上演。史料载,在大批难民和兵丁之间,书籍的功用常常被这样描写:“籍裂以为枕,爇火以为炊”。典籍、书籍只是露宿时的垫枕、做饭时的柴火。
还有一种可能性极大,我在《明朝那一场浑水》一文中也写过原因。史载:“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7)六月二十五日晚子时至次日午,大雨,汧、晖(今千河、冯坊河)二水暴涨,冲毁县城,知县张涵溺毙,民漂死者无计。”我推断,存放在署衙的文史资料等一并被那场浑水冲走了。
县志,是一个县历史、地理、风俗、人物、文教、物产等千年时间空间的浓缩,反映着这个地域的前世今生,是一个县的“家谱”。只有王国玮是发问后又行动的知县,公务之余,他访遗址、询故老、采旧闻,三年后终成《石门遗事》一书。经过明末清初的兵燹战乱,以及连年的荒旱,他上任时,全县人口仅存一千五百有三。无多少遗存史料,又无多少可访人员,闭着眼就能想到有多难。
八十一年后,新任知县管旆到千后索志,“遂以《石门遗事》暨《增补轶事》送阅”。他看过《石门遗事》后说:“土俗民情较为详尽,官师人物较为简略,缺漏多,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称不上志。”
管旆看到的《增补轶事》,是1711年(康熙五十年)江南宜兴岁贡吴宸悟任千阳知县时,对《石门遗事》的建置、官师、人物、选举等增补史料,又新增流寓、艺文二目。
罗曰壁到任后,认为《石门遗事》及《增补轶事》不全不详,加之断修已近百年。觉得他的前任们“典守者不经心焉”,也太不作为了吧。
罗曰壁又一次披挂上阵,重修志书。他取旧志与州府志详加参考,优者沿用,劣者淘汰。对旧志未记的内容,考遗迹、访名士,分纲列目记载。
全志设地理、建置、典祀、田赋、学校、官师、人物、选举、烈女、艺文、纪事、详异12卷96目,卷首附图14幅,约10万字。断限上至夏,下止道光二十一年(1841)。志成题名《重修千阳县志》,它是千阳历史上传下来的第一部称作“志”的县志。
为写这篇文章,《重修千阳县志》我翻阅了好多遍。在这些泛黄的古纸堆里,我读出了八字真言:脚踏实地,尽力去做。轻轻翻过的每一页,都浸润着他十年三个月在千负重躬行的心血。
五
罗曰壁,是一位典型的清代文人官吏,干的很多工作用文字记了下来,正是这一点为今天的千阳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比如:《书院》一文,记有新建启文书院的建筑物,经费来源渠道和数量,开支的名目和数额。增修、重修的县署、庙、祠、楼、坛等,也都用文字或碑记的方式留下了文字。
“下车伊始,集首事商议重修年久木朽渗漏的启圣祠,自捐廉俸四百金”。在他任内,面对捉襟见肘的收支,他没有压榨搜刮百姓,十余年任内前后八次捐银捐粮,创建书院、重修祠庙、裱糊县署、新建义仓(赈灾)。
从1910年(宣统二年)往前,千阳县志里记载了133名县令、伊、知县之名。即便是从事文史工作者,能记住名字的也两三人而已,绝大多数只在志书里留下三个或两个黑体僵字。
1804年罗曰璧考中举人,有学者对清朝考中举人的年龄论证过,平均在30岁,那么1830年来千任职时,他已到不惑之年。
兜兜转转,他任职的延川、平利、千阳几个县全是小县、穷县、偏僻县(作者查过陕西蒲城县和山西蒲县县志,没有他任知县的记载),经历使他更加清楚清朝后期官场升迁的诡异。因此,来千后,按当时官场或明或潜的规则,他即便不为自己搜刮些钱财,也完全可以磨时间混日子。但他没有,明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耗时、耗钱、耗人、耗力,修养、心态、担当、年龄催使他做的义无反顾、亲力亲为、倾囊而为。他做到了,他一一做到了。
罗曰璧在任时,幕僚们因他勤政尊敬有加,离任后,百姓们因感恩敬他为神,建“忠爱祠”记念他。在百姓心中,这位时常操着一口浓重乡音的知县,这位来自遥远西南边陲的外乡人,所做的爱民之事深深的镌刻在了千山之巅、千水之河和百姓心之尖。
建祠,这是百姓对办了好事的人最纯朴的一种虔诚膜拜。“有生佛万家之誉”,这是故乡旧景东县志对他的褒赞。(生佛万家,是指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出之宋·戴翼《贺陈待制启》:福星一路之歌谣,生佛万家之香火。作者注)。
自从司马迁写成《史记》后,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在做每一件大事时都会想到悬在头上的那支巨大史笔来。一支支细史笔也照样悬在各级官吏的头顶,在千阳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罗曰壁,赢得了身前身后名。
写于2024年2月26日夜